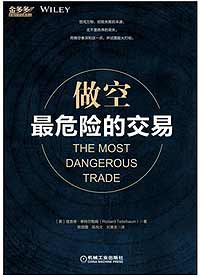|
|
|
作者:理查德·泰特尔鲍姆 |
早在2012年着手这个项目时,我就知道这些伎俩。毕竟,我在大学时就深谙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亚瑟?叔本华(Arthur Schopenhauer)的理论,而且痴迷于法国作家塞缪尔·贝克特(Samuel Beckett)的戏剧。后知后觉的我只能惭愧地说,我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出自功利主义。在2008—2009年的金融危机初降临时,很多学者和业内人士纷纷出手,推出很多令读者叫好的大作。我当时还在为《彭博新闻》(Bloomberg News)而奔波,不食人间烟火的主编让这份月刊杂志销量惨淡。不过,我还是为自己的这份工作感到自豪——在这里,我居然创纪录地发表了23篇头条报道。有些报道也对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进行了探究。不过,我的很多同行已成为查理-罗斯(Charlie Rose)脱口秀节目的嘉宾,更让我相形见绌的是,有些人的作品甚至已经被搬上银幕。 后来,约翰-威立出版公司(John Wiley & Sons)找到我,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做空的书,不过,我曾怀疑他们马上就会为这个想法感到后悔。
做空者原本应该是投资者中最另类的一批。当华尔街强大无比的营销机器摇旗呐喊、高调造势的时候,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噩梦惊醒市场的美梦,毫无疑问,他们是这个舞台上最光怪迷离的演员:一群生性孤僻、善于煽风点火或是愤世嫉俗的骗子和失败者。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?我的无法证实的偏执怀疑始于我在2012年1月的《彭博新闻》上发表的一篇调查性报道。2008年7月,美国财政部长亨利-保尔森(Henry Paulson)亲赴伊顿公园资本管理公司(Eton Park Capital Management),约见了一些对冲基金管理人及华尔街大佬,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自高盛,而保尔森则在1999—2006年担任高盛的CEO。据与会人士透露,这位财长向他们透露了极其重要的内幕信息——政府正在筹划接管作为抵押贷款担保机构的“两房”,也就是说,政府将接手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的股权。我在报道中援引法律人士的观点称,保尔森透露这个消息显然有违法之嫌。但保尔森后来又说,美联储不会采取类似举措。 随后,相关消息再无下文,直至2012年9月,《华尔街日报》称,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(SEC)已对该事件启动调查程序。当时,我为撰写本书而休假,而按业内常规,《彭博新闻》也未做进一步报道。于是,证交会的调查似乎并未给市场带来涟漪。
唯一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,就在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发表后一个月左右,当时我依然在休假,彭博总部却突然通知我被降职,新的工作几乎相当于一个初级数据录入员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他们却忘记调整我的高级作者头衔。当然,当时很多人都被降职。直到后来,彭博的工作人员才透露,当时的纽约市市长迈克尔·布隆伯格与保尔森有生意往来。实际上,他们都在一家名为“风险经营项目”(Risky Business Project)的环保组织担任主席职务,该组织的其他负责人还包括前对冲基金管理人、曾经在高盛工作过的托马斯-斯泰尔(Thomas Steyer)。 如果将本书的目的归结为记述这段涉及金融、监管、道德和社会的危机史,那么,这项有悖时运的工作似乎还算说得过去。很多人拒绝接受公开采访,有些人还算是客气,但同意只做私下讨论。很多时候我得到的都是些虚假信息,比如,一位采访对象给我提供了假地址,更多的人声称未保留以前的投资业绩。一位女性退休做空投资者的拒绝理由非常充分:她已经对做空交易彻底厌烦了,以至于不愿意和任何身高不足六英尺的矮个子男性进行交往 。
我曾邀请一位做空者到城区角落的意大利餐厅,听听他的“内幕消息”。吃过饭后,他提出,为了避人耳目,要到餐厅后面一个黑暗、废弃的停车场去聊这些事。一句话,那段时间让我心力交瘁。 但坏消息接踵而来。我在格林尼治住的公寓楼外墙正面亟待维修,总计花销高达3000万美元,维修工人们可也绝不心慈手软。在达拉斯的一次重大会议前夜,超级飓风“桑迪”席卷了纽约,我搭乘的航班被取消,计划好的采访也因此而泡汤。而洪水切断了供电,迫使大批老鼠涌入公寓,这些老鼠和我同在屋檐下,这也让公寓的修缮工作成为最紧要的事情。 幸运的是,我已经拥有了一批出色的虫害杀手,因为我时常住进臭虫出没的便宜旅馆而把这些臭虫带回家,他们经常来我家消灭这些虫子。有趣的是,这些虫子似乎对我的采访记录本和书里的漫画特别感兴趣。在我的做空者花名册中,最后一个接受采访的人同意在2013年上半年会面。当时,我的工作不只是被拖延了几周,而是拖延了几个月。和很多事情一样,这个项目同样让我感到羞辱和难堪,但更艰苦的经历还在后面。 2013年7月5日,绝大部分报告和写作均已完成。我的休假即将结束,我的数据录入员的新工作即将开始。 电话铃响了,是从医院打来的。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,女儿尼娜患感染性休克,她随后把电话递给医生。“病情很严重,”医生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恐慌,“真的很严重。” 毒素已经遍布了尼娜的全身,而且治愈的机会已经很有限了。医生告诉我,时间每过去一小时,死亡的危险就增加20%。 不过,随后的一系列手术似乎还算成功——尼娜在随后几个月里将在重症监护室度过。
我回到《彭博新闻》上班,开始了自己的数据录入工作,但每每想到还在医院里的尼娜,我就很难静下心来,也让本书最后几章的创作难以为继。好在尼娜的病情持续好转。 但随后却传来一系列与本书不相干的人的死亡事件:先是我的一个表兄(死于心脏病),而后是90岁的姨妈,最后是我在《财富》杂志工作期间遇到的第一位编辑、59岁的约翰-库仑(John Curran,死于肌萎缩侧索硬化)。与此同时,我的信息来源以及即将采访的人物也相继去世:《巴伦周刊》(Barron)杂志87岁的艾伦-艾贝尔森(Alan Abelson)死于心脏病;尼克斯基金公司(Kynikos Associates)的道格?米利特(Doug Millett),49岁时死于唾液腺癌,他在揭露安然财务欺诈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我本来就已经心怀疑虑,而这一系列事件则让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迷信。 2013年11月,彭博新闻社解雇了我,当然,和我一起被解雇的,还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记者。尼娜马上就要接受下一次手术,而且是一次费用极其高昂的手术(尼娜在医院的第一天花费了330637.54美元)。当然,我不知道她的下一步治疗是否会影响到工作。做空者让我知道,妄想狂患者随处可见。一位做空者告诉我:“你看到的事情并非如你所见。” 虚构和妄想注定不攻自破。恶有恶报,这就是伤痕累累的做空者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。或许他们可以赚上一两次,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?